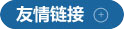这不是夏虫不可语冰的时间限制,也不是井蛙不可语海的空间阻隔,而是人性,是智慧。
一、没有利益的空言,说服不了人韩王为了耗费秦国国力,让秦国无力东出伐韩,自作聪明地派遣水工郑国去秦国当间谍,游说秦国修建工程浩大的水渠。秦国信以为真,命郑国修渠。结果,水渠还没修好,郑国的阴谋就被秦国识破了。然而,秦国不仅没有处决郑国,反而还让他继续主导修渠,最后还用郑国的名字为渠命名,称之为「郑国渠」。由此可见,岂是水工郑国在水利工程之外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雄辩之才,能把秦国忽悠瘸了吗?当然不是。事实上,秦国的决策层都是明白人,不管郑国最初的目的是什么,修渠都是符合秦国实际利益的。果然,水渠建成之后,关中变成千里沃野,再无饥荒之年,秦国因此富强。
甘罗,原秦国相邦甘茂的孙子,年仅十二岁便被嬴政派遣出使赵国,仅凭口舌之利就让赵王割让了五座城池。难道甘罗真有如此才智,可以摇动三寸舌,不费一兵一卒就白白得赵五城吗?若他十二岁就能有如此成就,为何之后史书中再未记载他有其他功绩呢?其实,赵国之所以愿意割让城池,是因为秦国许诺帮助赵国攻打弱小的燕国,让赵国可以不用担心秦国会趁火打劫,放胆出兵攻燕。结果,赵国夺取燕国三十座城池,并将其中的十一座分给了秦国。这是利益促成的共识,而非甘罗口才之功。
苏秦,战国著名的纵横家,曾担任六国合纵的领袖,使得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兵函谷关,其游说能力可见一斑。然而,当初他以连横之策游说秦惠王时,却碰了一鼻子灰。那时,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,正痛恨着这些口舌之士,苏秦就来了。只能说来的也真不是时候。苏秦一连上书十来次,也没能说动秦惠王,最后连活动经费都没有了,只得卷铺盖回家,这才有了后面「头悬梁锥刺股」的故事。这并非是苏秦能力不够,只是未能与秦惠王达成利益的共识罢了。
二、捭阖之术的原则,是寻求共赢何谓捭阖?南朝陶弘景的解释最为经典。他说:「捭就是拨动(引导),阖就是闭藏(闭嘴)。凡与人谈论事情,如果感觉彼此立场一致,就主动引导对方多说话,让对方也能感受到这一点;如果摸不清楚对方的立场,就索性闭口不言,让对方多说话,然后暗中揣摩彼此之间的分歧。」
简而言之,捭阖之术不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去说服对方,而是尽可能地寻找双方都可以获利的那个点。
就像苏秦,以连横之策游说秦国而没有成功,但以合纵之术游说六国却功成名就,本质上就是这个道理。
商鞅入秦游说秦孝公,和孝公谈了四次才得成功。第一次,他试探性地以五帝之道进行游说,结果讲了半天,孝公听得昏昏欲睡。第二次,他闭口不谈五帝之道,转而改用三王之道继续游说,依然未能打动孝公。第三次,他又改用春秋五霸之道,孝公表现出了些许好感,于是他就知道下一次该怎么说了。等到第四次跟孝公交谈时,商鞅以强国之术游说孝公,孝公大悦,商鞅也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
试想,如果商鞅一开始就坚持以帝王之道游说孝公,甚至认为自己的坚持会打动孝公,而不去揣摹孝公的心思,其结果必然会和苏秦一样,历史上也就没有商鞅变法这回事了。
在汉武帝时期,公孙弘每次上朝议事时,自己都是只开个头,然后让武帝自己做决定,也从来不跟别人面红耳赤地争论。有时候所奏之事不被武帝采纳,也不会再继续为自己辩白。大臣们上朝之前经常商量好要向武帝汇报的事情,等到了武帝面前,其他人一通输出之后,公孙弘但凡发现武帝有不同的意见或想法,便会当场反水,然后顺着武帝的意思来。后来公孙弘官至丞相,封为平津侯,并得善终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要知道武帝一朝,丞相换了十几个,寿终正寝的可不多。公孙弘的能力,肯定不止嘴皮子功夫。
三、最难得的,是居中的智慧有些人自矜其能,总认为自己能言善辩,动辄就要跟人抬一抬、杠一杠。杠赢了就觉得自己才智过人,杠不赢便指责别人顽固不化。这种人浅薄又可笑,遇到这种人,避而远之即可,切莫浪费时间。
另外有一些人,他们是只以对错来评判世界的二元精英主义者。在这些人的心中,自己拥有专业且权威的判断和分析能力,即使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也是如此。上至国家大政方针,下到亲朋好友的鸡零狗碎,都需要他们来指点迷津。他们改变不了环境,也说服不了别人,更释怀不了自己。眼里看到的不是愚就是贪,不是贪就是坏,简直就是「世人皆醉他独醒,世人皆浊他独清」。
这种人其实就是头脑比较简单,处理不了复杂的事情。也很难让他们理解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里,很多事情是需要兼顾多方利益之后,曲折辗转才能做成的。
杜预深得晋武帝司马炎的信任,他不但是武帝的姑父,后来还带兵平定东吴,可谓是要能力有能力,要关系有关系。但自己领兵在外,还要时时贿赂洛阳显贵。有人问他为何如此,他说,「我不求这些人说我的好话,只求他们不要等我在外征战时陷害我就好了。」
杜预尚且路坎坷,常人岂能有坦途。
己要先为人着想,人才能为己所用。这才是与人沟通、与人相处的核心原则。捭阖之术,即是如此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